在人们爱上咖啡的味道之前,喝咖啡仅仅是一种日常,用以摄取咖啡因。和我们生活中许多事情一样,“享受”是一件通过时间慢慢积累而成的事情。随着你的体验和阅历不断增多,你会更加懂得如何“享受”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,人们每天起来所饮用的咖啡,主要来自于这两个区域:以日晒处理为代表的埃塞俄比亚哈拉尔,和以水洗处理为代表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。
可能是出于机缘巧合,也可能是前生注定,出身卑微而贫贱的咖啡,现今成为了千家万户的必需品以及全球性的贸易产品,而这两个标志性的咖啡产地也与咖啡本身有着剪不断的联系。

很多有关咖啡的故事都被一定程度上美化成了传奇或者神话, 而往往缺少了对真实的刻画。当然, 我相信咖啡的故事是值得传颂的, 只是它既得满足人们对于理想的憧憬, 也要尊重它所涉及的事实。
那么我想和大家探讨一番——咖啡,这种被烘焙过的水果种子,为什么会分布在全球各地,又是为什么会让人们念念不忘,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。
#闪亮登场
阿拉比卡的故乡是位于埃塞俄比亚西部和南苏丹的Boma高原[1],直到现在,这里依旧是咖啡原种的自然基因库。阿拉比卡咖啡有很多分支,大部分都可以在非洲大陆找到。Canephora品种(罗布斯塔)最早发现于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, 而利比里卡品种则如其名,是在利比里亚被发现的。
曾经人们食用咖啡的方式,和今天完全不同。以前,人们会把咖啡果裹上油脂,当作口粮食用,也会直接水煮或咀嚼,还会专门将咖啡果的果肉发酵成一种类似酒的饮料。Haya人(主要是现在坦桑尼亚西北部的人) 曾经把交换咖啡豆当作一种问候,但埃塞俄比亚的Oromo人认为,咖啡是一种神的馈赠,种植咖啡被视作是对神灵的不敬[2]。所以,咖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野生状态,而不是作为一种作物,为世人所知晓。
埃塞俄比亚科比克人的阿克苏姆帝国,是否在公元6世纪占领阿拉伯的“失乐园”,也就是今天的也门时,便已经把咖啡带到了那里? 虽然很多人不太相信,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在各种传说中,我们可以看到端倪:索罗门王使用咖啡来治愈瘟疫;Kaldi发现吃过咖啡果的山羊行动亢奋;大天使Gabriel甚至将咖啡赠给一位窘困的预言家——默罕穆德;Sheik Omar被逐出摩卡城,仅靠咖啡果得以存活数日。

据史实资料记载, 咖啡实际上是在15世纪中叶,由亚丁伊斯兰教主Sufiimams[3]带到也门Aden港的。这是咖啡“ 离开” 故乡, 走向世界的开端。
在咖啡被发现的历史过程中,无数的偶然让咖啡普及成为了必然。随着历史的推进,世界不断融合,伊斯兰世界在经历了长达几世纪的文化复兴后逐渐崛起。15世纪,在Rasulid王朝开明的统治下,也门的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灌溉技术的发明[4]和使用使得咖啡种植变得更加容易,家家户户都能种植咖啡了。咖啡甚至还冠用了阿拉伯半岛的地名,被称作为阿拉比卡咖啡。当时,人们通过晒干咖啡果肉而制成的混合香料饮品, 则被称为q’shir。很快,用来烘焙以及研磨的土耳其咖啡壶( 一种特制的黄铜或红铜茶壶)流传开来。
那些在奥斯曼帝国松散统治下的国家们逐渐地对咖啡的制作方式、口味,形成了一致的偏好。咖啡于是被带向了世界,也有了世界上第一家咖啡店,咖啡商品化的大门从此被打开。但是出于宗教原因,咖啡曾一度被限制。Sultan Murad 四世[5]就曾下令禁止咖啡出口,据传,他还曾亲自乔装到康斯坦丁堡街头视察,如果看到售卖咖啡者,就亲自斩首。也门也曾借由其摩卡港全面垄断咖啡交易,这种垄断直到18 世纪才被打破。今天的也门咖啡依旧被称为摩卡,因其特有的巧克力、香料、浆果和葡萄酒风味而闻名,价格不菲,为人追捧。
#哈拉尔, 通往东方的咖啡之门
也许,全世界没有比哈拉尔更特殊的咖啡了,它极有可能是最早被非洲以外的人品尝到的咖啡。虽然,位于埃塞俄比亚东部的哈拉尔是一个边陲之城,但它曾是伊斯兰的精神中心与贸易港口。15 至16世纪,这里的文化曾达到顶峰。非洲东部和阿拉伯半岛也因为哈拉尔而被联系在了一起。

哈拉尔位于东部,距咖啡的故乡——西部的卡法(Kaffa)王国非常远。但其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,及在文化和经济上的重要作用,引来了也门的商人和伊斯兰的教士,并使他们开始接触咖啡,在咖啡的传播和商品化上,哈拉尔有着历史性的意义。
也许,哈拉尔咖啡曾经最有影响力,也最让人记忆犹新的咖啡。它独有的日晒处理方式(咖啡在收获后,直接进行晾晒处理)于上世纪80至90年代达到了顶峰,也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。风味上,哈拉尔咖啡以其独特的蓝莓风味而极具辨识度。对于喜爱咖啡的人来说,哈拉尔咖啡就如同瑰宝,你很难用言语描述其价值,唯有用心体会。
遗憾的是,在21世纪初,哈拉尔咖啡逐渐失去了它的其魅力。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耶加雪菲和西达摩,在2008年,埃塞俄比亚又启动了ECX交易制度,贸易商们很难从单一产地再找到好的咖啡。于是,哈拉尔咖啡逐渐退出舞台,成为咖啡人心中一个不可磨灭却难再重现的记忆。不过,这种希望从未殆尽。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,在过去的十年里,埃塞俄比亚对ECX交易制度做了诸多调整。通过咖啡人的口耳相传,以及一些还能被追溯到的信息,我们可以借助各种现代数据手段和灵活变化的贸易方式,来尝试唤醒我们对哈拉尔咖啡的味觉感受。
#印度尼西亚, 传播到西方
可能再也没有哪种咖啡能像印度尼西亚的“湿刨咖啡( 通过水洗处理的咖啡豆)”那样,与哈拉尔咖啡的风味迥异。历史似乎也为印度尼西亚转了个弯,将咖啡专程从也门送到了这个太平洋的小岛上。
咖啡“偏爱”着多元文化的交汇:它既是一种艺术,又是科学; 既是工艺品,又是大宗商品; 既是带刺激作用的饮料,又是让人欲罢不能和品鉴的尤物。从“离开” 故乡埃塞俄比亚, 再到种植地也门, 咖啡正与更广阔的世界交汇。当然,这也要得益于欧洲的殖民者。
当时,也门通过禁止出口咖啡种子来垄断咖啡的贸易。最终,他们的垄断被荷兰人打破了。据记载,在1616 年时,荷兰商人Pietervanden Broecke到访摩卡港,偷偷将一颗咖啡树连根拔起,并走私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植物园中[6]。到17 世纪末, 荷兰人还将咖啡树种到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西海岸。
1699年,咖啡从印度的Malabar 海岸被移种到当时荷属东印度的巴塔维亚(今天的雅加达)的爪哇岛,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。历史好像是在捉弄我们,虽然咖啡途径了印度和斯里兰卡,但是爪哇却成了继阿拉伯半岛(阿拉比卡咖啡)后,再次给咖啡命名的地方(爪哇咖啡)。

这个由也门途径印度,最终到达爪哇的咖啡,也成为了接下来一个半世纪, 唯一真正走向世界的咖啡品种。这种咖啡,就是隶属于阿拉比卡咖啡,为我们所熟知的铁皮卡品种。后来,这个树种再次回到欧洲阿姆斯特丹,以及巴黎的植物温室,随后,又被带入了美洲。而阿拉比卡的另外一个品种——波旁种,则是在荷兰的植物园,由爪哇的铁皮卡咖啡培育而成。后来,波旁种还作为礼物,馈赠给了法国王室。
印尼咖啡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发展路线。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荷兰殖民者想在印尼群岛推广咖啡,并逐渐地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。到了1725年,他们要求当地人广泛种植各种经济作物,包括咖啡、甘蔗和棉花[7]。但实际上直到1830 年, 荷兰人的“ 定植制度” ( 要求殖民地居民, 定量定品种的种植作物)才真正被实施。由于荷兰乃至欧洲不断增长的咖啡需求, 爪哇、苏门答腊、苏拉威西地区人们的种植权利被殖民者剥夺, 并收归殖民政府管控, 即便是小农户也要按照要求种植经济作物, 并悉数上缴。
在印尼, 殖民者留下的印记不仅仅是作物种植领域,对咖啡产业也影响至深。爪哇咖啡作为殖民时期最主要的咖啡种植区,至今仍延续着它的地位。而古老的中介商运作方式, 则直接导致了印
尼用水洗处理方式处理咖啡( 在当地被称为“ 湿刨” )。这种处理方式能最大限度地节省种植者的劳力和时间。收获的咖啡豆先要进行去果肉处理,之后用羊皮纸包装好并销售给中介商,让他们去做进一步的处理。最后,去除掉羊皮纸壳,再完成对咖啡豆的干燥处理,咖啡就可以出口了。通过这种处理方式加工后的咖啡,口味独特,咖啡豆本身呈现出一种极其漂亮的绿色, 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门答腊咖啡。
不过,关于印尼咖啡,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。在咖啡被种植到印度尼西亚后的一个多世纪里,印尼咖啡一直是国际咖啡市场的主角,直到1869年,一场极具危害性的叶锈病灾[8]席卷了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咖啡种植区域。突然之间,咖啡生产几乎都退到了西半球。直到罗布斯塔咖啡品种的引进,印度尼西亚的咖啡市场才得以重振,也培育出了罗布斯塔与阿拉比卡的杂交——提姆品种( Timor )。后来, 大部分地区开始种植具有抗叶锈的咖啡品种,只有极少数偏远的高海拔地区还在种植铁皮卡,最终,铁皮卡退出了印尼的舞台。
目前,全世界有很多来自于火山岩岛屿的咖啡,虽然它们都有一些共性:低酸度;带有泥土味和甜味。但在印尼,特别是苏门答腊地区,咖啡仍具有独特的风味。那里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水洗处理方法,而其独特的地理环境、强悍的抗病虫能力,使得这里的咖啡在全世界咖啡产业中都是独树一帜的,在目前的精品咖啡领域中,也仍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。不过,苏门答腊咖啡含有较高的咖啡因, 并不适合心脏不好的人饮用。
21世纪初以来,精品咖啡的概念正以迅猛的速度席卷全球咖啡行业。即便如此,目前咖啡品种的多样化依旧是基于过去的原种咖啡,就像哈拉尔咖啡和苏门答腊咖啡。他们独特的风味激发了人们对于咖啡的好奇和热情, 也成就了它们传奇的过去。没有它们,我们今天就不会拥有这么一种值得被挚爱的饮品。
资料参考来源:
[1] F.Anthony, et al ., “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Coffea arabica L.varieties revealed by AFLP andSSR markers.”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(February, 2002). http://horizon.documentation.ird.fr/exl-doc/pleins_textes/pleins_textes_7/divers2/010029197.pdf
[2] Topik, Stephen. “The Making of a Glob al Commodity | Part 1:Out of Arabi a” SCA News. (October, 2013) http ://www.scanews.coffee/2013/10/04/the-making-of-a-global-commodity-out-of-arabia/#4
[3] Robinette, G. W. Why Drug Wars Fail: A Study of Prohibitions Vol 1. , Graffiti MilitantePress (2012) 5 17-521.
[4] Caton, S teven C. Yemen volume of Midd le East in Focu s ABC-CLIO (2013) 52-54.
[5] Weinberg, Bennett Alan & Bonnie K. Bealer. The World of Caffei ne. Routledge (2001) 15.
[6] Ebert, Andreas W., et al. Securing Our Future, CATIE’s Germplasm Collections. Turrialba (2007) 21
[7] Kahin, Audrey.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Indones ia, Third Edition. Rowman & Littlefield (2015) 99.
[8] Kushalappa, Ajjamada, C. & Albertus B. Eskes. Coffee Rust: Epidemiology, Resistance, and Management. CRC Press, Inc. (1989) 178.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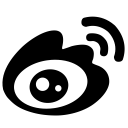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NO COMMENT